播客兴起:“听觉文化”的回潮

2020年这个注定不平凡的春天,除了疫情之外,一些事物的回归与再创造同样在发生。一档由芒果TV独家制作的声音类真人秀节目《朋友请听好》,将电台这个听上去有些过时的事物,再一次拉回到大众的视野。原子化生存的当下,许多人都期待着这样温暖又治愈的声音,是通勤路上的陪伴,亦是繁忙生活的慰藉。大众对“声音”的需求似乎再度回归了。在这个“视觉霸权”的时代,声音经济的复兴昭示着什么?各种电台、播客、有声书的流行又意味着现代人的何种需求?

01播客——在进化中走来的新听觉文化
作为一种小众文化,播客这个概念最早诞生于2004年2月12日。英国卫报在一篇题为《听觉革命:在线广播遍地开花》的文章中最早提到podcasting这个概念,该词意指一种新的数字广播技术,听众可以在移动设备上听取广播内容,并且可以任意选择或订阅。
然而,相比于诞生之初的令人瞩目,随后的十年,播客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,投资和消费市场被大型的视频网站占据。直到2014年,《Serial》横空出世,以广播剧的形式呈现犯罪小说的紧张情节,吸引了大量的听众,成为一档现象级的播客。2015年,由于商业化生产实践和大众媒介消费的快速发展,“播客第二时代”来临。十年的发展中,播客逐渐拥有了完整的产业链和受众,也积累了许多高质量多元化的内容。而爆款播客的出现,则成为了吸引新流量的契机。同时播客制作的内容和数量以此为节点开始上升,广告商也随之跟进,提高了播客的营收能力。
2013年以来,国内迎来了播客的全面兴起。喜马拉雅、Himalaya相继上线,播客平台进入井喷期。从2018年开始,中文播客越来越多地出现,有人将此归结于知识付费音频所带来的“听觉经济”效益,也有人认为是各类视频的狂轰滥炸,让审美疲劳的人们暂时抛弃视觉接收,从耳朵的聆听中寻找另一种安慰。
而2019年是中文播客发展的一个节点,注册数和播放量迎来了明显增长,像《反派影评》、《忽左忽右》、《博物志》、《剩余价值》这样的播客,因其高质量的节目内容,有见地有智识的评论吸引了听众关注。聚集了一大批喜好相似的忠实粉丝之外,他们也不断探索盈利的可能性。即使播客在商业市场仍属相对小众的领域,但“听播客”确实日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。
02当下中国播客产业——萌芽、初兴与困境
想法成型,开机录音,后期剪辑,上传分发,这是一期播客节目相对固定的制作流程。通常一小时的节目,制作周期在一天到一周不等。在追求效率和性价比的时代语境下,播客制作者这个身份在很长时间里,只是少数人的选择。
在播客界,《反派影评》是另类的存在。《反派影评》是2016年4月开播的一档影评类节目,主播波米可以说是中国最神秘最具个性的顶尖影评人之一,从节目开播以来,就以扎实的专业能力,和敢说敢评的自由风格著称。

《剩余价值》在2019年开播,内容多为泛文化类讨论,相比之前一些由个人兴趣驱动的播客,《剩余价值》有着更明显的媒体属性,常常触及公共议题,如针对去年年末发生的PUA和家暴事件,《剩余价值》都做出了评论,又或者在今年新冠肺炎爆发之后,邀请了历史学家罗新讨论。在该期节目中,从瘟疫封城聊到语言污染,从战时状态聊到民族主义,从饭圈用语聊到个体叙事,最终,所有的一切收束于“人”作为鲜活个体的独立存在价值,不论地域,不论种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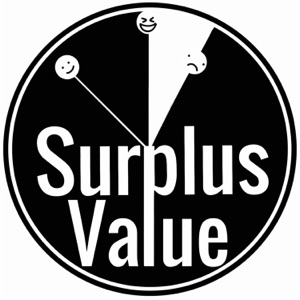
《无业游民》是一档温暖的播客,大多节目都是分享主播和嘉宾自己的经历和心绪。生活化的记录,分享个人心情,也聊一些由此而想到的电影、音乐、书籍。即使介入公共议题,《无业游民》选择的角度也非常柔和。作为主播之一的科长认为2019年中文播客就已经出现媒体化的倾向,制作者充分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,关注社会热点,对一些文化现象发表评论,“很多播客都是媒体人做的,难免带有这种属性”。

即使是这些内容极为优质的播客节目,也需要面临运营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困境。放眼中国播客业,其仍处于起步阶段,盈利模式尚未成熟,主要依靠粉丝打赏,版权问题依然处于灰色地带,甚至连录音环境也无法得到良好的保证。
大多数播客都是家庭制作,最大的烦恼是录音环境和邀请嘉宾。请嘉宾是困难的,几乎所有播客在起步阶段,嘉宾都是主播身边的朋友。朋友间一来比较熟悉,聊得自然,不容易冷场,最重要的是请朋友不要钱。而主播和嘉宾的性格往往奠定了一档节目的气质。
03听觉文化的回潮——打破“视觉霸权”?
听觉消费的再度兴起,可以看作是对长期以来“视觉霸权”的一种挑战。
移动互联网时代,数字化声音世界的互动及共享性,迎合了人类听觉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社会性,从而创生出了敞开式的在线虚拟公共听觉空间。在这里,大众不只是单方向地接收听觉内容,而是在双向互动中进一步传递或制造。如朋友圈中常见的音乐分享,就是一种个人对自己音乐审美的塑造和将音乐再次传递的过程。再如轰动一时的网易云音乐评论区里百万点赞评论,人们在虚拟的听觉小区中找到自我认同与归属感,每一次分享,每一次点赞,都是一次寻找自己的兴趣部落的过程,也是一次通过与他人的交互关系,从而更好地塑造个人音乐审美的体验。与此同时一些付费音频栏目的兴起,也成为了人们新的听觉活动与听觉名片,每天在上班、上学路上戴上耳机,打开听书或名人讲堂音频,在数字化声音陪伴下进行碎片化学习,成为了当下流行的知识习得方式。商家们贩卖着轻量级、碎片化的声音,大众也乐于接受并认同这种听觉消费,同时还给自己贴上最时髦的听觉文化标签,手指一点,转发分享,更多人被吸引到了这共同的听觉群落。
听众与制作者之间的虚拟连接,是否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通?我们不得而知。跨越异地与屏幕,在感受和认知层面上,两者之间的距离因人而异。毫无疑问的是,以播客节目为代表的听觉互动文化产品的出现,使得听觉文化在当代的复苏成为更大的可能,人与人之间单一诉诸图像的情感交往方式,得到了听觉维度的补充与拓展。现代人类可以得到慰藉的,除了6英寸屏幕上的视觉狂欢,还有一小时内通向耳朵的情感知识双向交流。